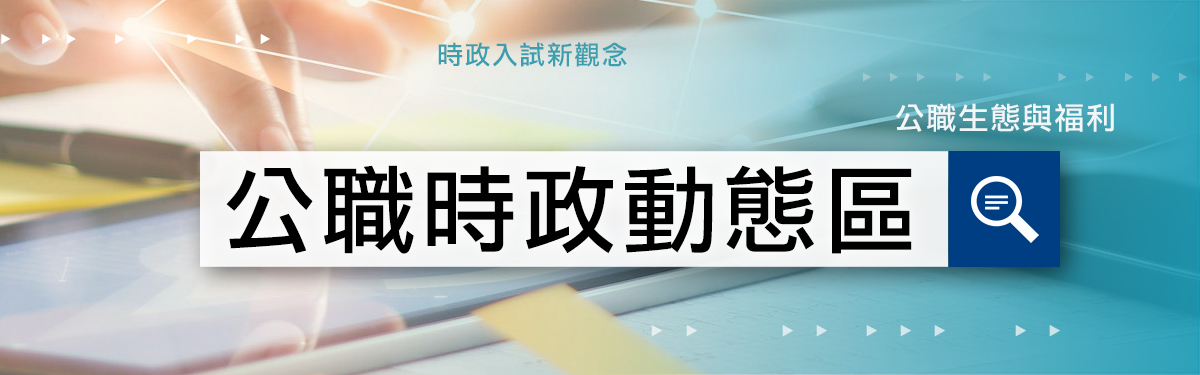美國聯邦參議院於9月30日進行延長撥款法案的表決,但因為近年來共和黨與民主黨,兩黨的矛盾愈加激烈,目前在平價醫療法案是否納入低收入戶家庭之補助產生激烈爭執,使得美國聯邦政府必須在10月1日正式停擺(government shutdown)。而所謂的停擺並非真正的所有聯邦政府部門與雇員完全停工,而是政府機關暫時關閉「費必要服務」,其他如:醫療、氣象、郵政、軍事、航空…等,仍會維持最低度的運作,但若預算案遲遲未通過,上述公共服務有可能會停止,目前聯邦政府尚未發生此情況。這並不是美國聯邦政府第一次的停擺,自從《1974年預算法案》生效後,美國聯邦政府總共停擺過22次,停擺最常一次的是上一次川普任內自2018年底至2019年初,由於共和黨與民主黨於美墨築牆的經費上無法達成共識,因此聯邦政府停擺了跨年度的35天。
美國聯邦政府與議會之間的關係牽涉到眾議院與參議院中民主黨與共和黨議員人數,以及可能的相關重大法案爭議,最後立法權透過杯葛預算的方式迫使行政權尋求協商或屈服。但是行政權的停擺說明著許多公共服務必須暫時中止,政府機關公務員被迫休無薪假。如此的情況肇因於美國的憲政體制,基本架構由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與監督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的概念組成,行政權與立法權相互監督制衡,且美國憲政體制並沒有不信任投票制度,因此遇到府會爭議僅能仰賴兩者及執政黨與在野黨的協商,而在背後督促協商盡快完成已恢復政府運作的壓力即「民意」。
相同的,我國地方政府體制亦類似於前述的權力二元制度,行政權由地方政府所擁有,立法權則屬於地方立法機關的職權,雖然我國地方自治制度中有立法權對行政權的「質詢」,但相同的沒有不信任投票制度,當府會兩者遇到總預算爭議時,應該怎麼處理?在討論處理方式前,首先理解過往曾經發生過哪些府會衝突(劉文仕,2022):- 代表會審議公所年度預算,認其收支不平衡,授權公所自行調整,惟公所遂大幅度刪減代表會經費,致使其無法正常運作。
- 公所預算近兩百科目經費遭代表會分別刪減至1元及2元,公所提覆議,代表會僅分別就各項目再加1元。
- 公所拒絕撥付法定義務性支出公款予民代表會,致使其員工薪資及代表研究費等無法發放。
- 公所預算被刪歲入(出)各約11億元,並決議由公所本自行調整,公所竟將代表會預算由2,100萬刪減為220萬。
- 鄉(鎮、市)年度總預算雖經縣府核定,公所卻遲不發布。
- 年度預算經代表會審議通過,並由公所公布實施。惟公所事後以「專案管控」名義緩撥或不撥代表會經費。
- 2010年時,白沙鄉代表會將公所編列之臨時人員薪資全數刪除,後經白沙鄉公所提起覆議,代表會卻維持原決議,公所遂依地方制度法第40條第5項,報請澎湖縣政府邀集有關機關協商;次年,鄉公所編列之年度總預算,僅將民代表每人每月之研究費編列1元,作為報復,且拒絕列席定期會做施政報告;2013年則是代表會大幅刪除鄉公所預算剩1/5,2014年1月1日,鄉公所自行斷水斷電,停擺公務作為抵制。
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0條第1項規定:「直轄市總預算案,直轄市政府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月前送達直轄市議會;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二個月前送達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直轄市議會、縣(市)議會、鄉(鎮、市)民代表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成,並於會計年度開始十五日前由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發布之。」前述規定訂有地方政府總預算審議期限,惟實務上因農曆新年或政黨輪替的因素,並不會於前述規定期限內完成,而後由臨時會審議完畢。然當府會之間對總預算法案有所爭議時,處理的方式如同前述白沙鄉公所及其代表會之案例,依據地方制度法第40條第4項規定:「直轄市、縣(市)、鄉(鎮、市)總預算案在年度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成審議,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得就原提總預算案未審議完成部分,報請行政院、內政部、縣政府邀集各有關機關協商,於一個月內決定之;逾期未決定者,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明顯與美國聯邦政府與議會間的爭議處理方式不同,我國地方自治發生府會爭議時依賴上級自治監督機關的介入協商,惟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作為邀集協商機關,應有何種協商作為?內政部函釋認為,應於尊重地方自治團體與維持政務正常推動之法律義務上為適當裁量,其得具體協商或逕為決定之預算項目或額度,自應與爭議之預算具有事實或法律上關連性,且以地方自治團體政務得以正常推動所必要者為範圍,並參考總預算案編列所根據之事實及參與協商機關之意見,而為協商或決定,以確保地方自治之有效運作。
前述規定與函釋看似給予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介入一個合法的途徑與應有作為之規範,然而卻有許多值得非議之處(方彥鈞,2025):- 即便內政部函釋協商機關應有之作為,但未見地方制度法有相關規定,意即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介入後並無法規範其角色與作為,僅有函釋不足以為協商制度訂下法制規範架構。
- 又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介入協商,明顯沖淡地方行政權與地方立法權兩者對於推動地方自治之民主意涵。首先,地方自治所需之財政係地方自治的核心權之一,豈能由毫無民主基礎之上級自治監督機決定之?再者,地方政務推動若因總預算案卡關而有所延誤引起民怨,這些民怨應直接反應於其選出之地方民選公職人員,包含地方行政首長與地方民意代表,而非由上級自治監督機關取代他們的政治責任。
- 最後,若邀集協商機關介入邀集協商後一個月未達決議,逾期由邀集協商機關逕為決定,如此的總預算案可能地方行政權無奈,地方立法機關的職權亦實質被剝奪,若對該決定有所異議,認其有不當或違法之處,以目前地方自治法制架構而言,毫無任何可茲地方政府提出救濟之手段。
綜上,我國目前地方自治法制中化解地方府會衝突之機制,具有明顯的法治與民主意涵上之缺陷;甚至上級自治監督機關介入後仍無法解決,長期下來影響地方居民權利及地方發展甚鉅。趙俊人(2000)參考日本與韓國之地方自治經驗後提出五項改革的建議;另劉文仕(2022:386-387)則是以行政至上的日本模式說明其解決衝突的機制,該模式縮減議會權力以避免府會衝突。這些都是未來地方府會衝突化解機制的法制面修正之重要建議。
- 參考資料:
- 方彥鈞(2025)。地方政府與政治(含地方自治概要)。高點。
- 劉文仕(2022)。地方制度法釋疑(增訂第五版)。五南。
- 趙俊人(2000年9月)。我國地方政府府會協商機制之研究。立法院。https://www.ly.gov.tw/Pages/Detail.aspx?nodeid=6586&pid=84171。
- 相關試題:
- 103原住民特考三等地方政府與政治第二題
- 107原住民特考三等地方政府與政治第二題